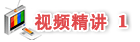第三节 基本权利的保障、界限与效力
一、基本权利的保障
宪法上规定某种基本权利,必须在实际上也能保障这种基本权利能够落到实处,后者才更重要。得到保障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一方面,即使一国的宪法对基本权利规定了详细的权利规范体系,没有完善的保障机制也就只能停留在宪法文本的纸面;另一方面,宪法文件不可能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完全详尽和细致的规定,而在具体的权利保障过程中,扩展权利的内涵,丰富权利的类型,美国宪法的运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重要范例。例如,美国对其宪法文件中有关“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概念的发展,就是通过长期的美国联邦法院司法判例和实践得以推进与完善的。又如英国,甚至一直没有成文宪法典,却通过优良的宪政和法治传统,以及司法实践运行,实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
(一)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
对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效果,受到各国的保障模式的影响。日本一些著名的宪法学者将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区分为绝对模式、相对模式和折中型保障模式。
第一种是绝对保障模式,是指宪法文本中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其它法规范不能加以任意限制或规定例外情形的方式。美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其宪法第1条修正案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制定建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的法律以及对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或对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诉求冤情救济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法律。”这个条款被认为体现了绝对保障方式的观念。但实际上,在美国宪法的这一规定之下,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不加任何限制的理想,或许是空想。也就是说,绝对保障模式,不等于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绝对不限制,这首先是由宪法基本权利确定的。
从现代各国宪法的实施情况来看,在实际运作中,采取该模式的一般都实行具有实效性违宪审查制度。通过这种制度的机制,排除了其它法律规范对基本权利所可能施加的逾越了该项基本权利自身的内在制约的限度的、并不能被宪法所接受的那些制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是一种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由于绝对保障模式是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并通过宪法自身所设置的制度而实现的,所以又被称作是“依据宪法的保障”模式。
第二种是相对保障模式,是指允许其它法规范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加以直接有效的限制或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保障方式。采取这种模式也是宪法自身的一种选择,因此宪法本身就规定或默示了对自身所确认的某些基本权利可以进行限制。例如宪法文本中规定某种基本权利“其内容由法律规定”、“在法律的限制之内”或“在法律的范围内”予以保障、“其例外依法律规定”以及“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等等。这里的“法律”指的一般就是议会的立法,这都表明了宪法本身选择了相对保障的模式。由于相对保障模式是通过普通法律而非宪法自身来实现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为此又被称作是“依据法律的保障”模式。
德国魏玛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就属于这一类型,二战前的欧洲各国宪法、日本明治宪法以及我国民国时代的历部宪法,基本上属于这种相对保障模式。这个相对保障模式的形成,与欧洲大陆传统公法中的“法律保留”观念和制度息息相关。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上,法律保留原则表现为两种:第一是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法必须由普通法律加以规定,该意义上的法律保留被称作“规范保留”;第二是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通过普通法律,被称作“限制保留”。但是这种相对保障模式实质上使基本权利只能在普通法律的范围内得到保障。一旦法律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出现问题,则无法寻求宪法的直接保障和权利救济。
第三种是折中保障模式。上面两种模式“绝对保障”和“相对保障”并不能完全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宪法作为分类的单位。事实上,在一些国家的同一部宪法中,就既存在被绝对保障的基本权利,也存在被相对保障的基本权利。这就出现了一种介于绝对模式和相对模式之间的折中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既一方面存在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另一方面,宪法本身又将对某些基本权利的保障委托给普通法律。当代德国(二战后)基本法(1949年)所采行的基本权利保障模式就属于这种折中模式。
另外一种“制度性保障”,或者称作体制保障,同学们可以适当了解一下即可。二战后的“新制度性保障”说,将自由权利本身直接理解为一种“制度”,如出版自由就被认为是一种自由的出版得到保证的制度。
(二)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
我国现行宪法基本上没有明文规定对某种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法由普通法律加以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或实际上默示性地规定普通法律可以限制某种基本权利。然而,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层面上,以及实践中所形成的基本权利保障方式,则倾向于相对保障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行制度下,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都必须由普通法律加以具体规定才能实现。具体的运作技术是:宪法首先规定了基本权利,普通法律再依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具体的界定,然后在法律所界定的范围之内付诸实施和保障。
2、与此相适应,仅仅存在普通法律的权利救济制度,而不存在宪法上的权利救济途径和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国还未建立起司法上违宪审查机制。
3、在目前的法律下,普通法律上已有的救济制度也只适用于部分情形下的部分基本权利,而非所有情形下的所有宪法权利。例如,典型的是,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只受理行政机关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等若干基本权利的案件,而且侵害方式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
虽然,由于宪法文本中的权利规范的表述非常简约和抽象,且不具有直接可依据的用以追究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并予以相应处罚的强制性规范。为此,要保障各项宪法权利,该权利本身的内容就有待于具体的界定,但由“谁”界定、“如何界定”,则涉及至关重要的宪法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下,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行使宪法解释权(第67条),但在实践中,人大常委会不经常(很少)行使这一权力,通常也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项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进行逐一解释。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实施监督权加以实现(第62条、67条),但实际上这项权力的行使在技术上存在困难,也没有形成一种惯常的制度。同时,由于在我国目前未建立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本身甚至被认为不具有直接的司法适用效力。因此,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只能选择相对保障模式
。如何选择和确立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保障模式,这是当今我国宪法学理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必须加强我国宪法的监督制度,这值得大家思考。
二、基本权利的规范性界限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可以说都是有一定界限的,这种权利的界限就是该权利获得实现和保障的终点。
1、基本权利界限的意义有:
(1)基本权利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界限;
(2)基本权利的宪法学意义上的界限。也就是宪法规范的制约,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这种界限往往被表达为一种一般性的规范依据,例如公共福利条款、公共利益条款或者权利滥用禁止条款。我国宪法也在第5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根据这一规定,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可能发生冲突的临界点,就是基本权利的界限。
2、基本权利的界限具有下面两个主要特点:
(1)界限的相对性;
最重要的基本权利是没有界限的
(2)界限的具体性。即使某些权利具有界限,这种界限也是具体的。也就是,不同宪法权利的界限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不能一概而论。 内在的制约,是指宪法权利在其自身的性质上理所当然所伴随的、存在于宪法权利自身之中的界限。 外在的制约,是指某一权利的外部所施加的、并被宪法的价值目标本身所容许的制约。
3、处理的方法:“利益衡量”的原则
三、基本权利规范的效力
直接适用:美国民权诉讼等案件
司法能动主义
沃伦(Warren)法院(1953-1969)
司法保守主义
伯格法院、伦奎斯特法院
对私法领域:无效力说、第三者效力说